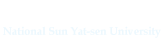成語和格言 中國詩的句法始於四言之端莊,歷經五言與七言之奇偶交錯,相反相成,而終於長短句之伸縮多姿。(中國時報)
作者:中山大學榮譽教授余光中
5新文學改用白話,不再寫文言,但是文言的智慧與語法卻靠數以千計的成語保留了下來,像一筆豐富的遺產,不用交稅,也無須兌現,口頭筆下,永遠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現金。
成語用在白話文裡,可以潤滑節奏、調劑句法、變化風格。我們很難想像,一篇文章能完全不用成語,因為那樣的文章必然累贅冗長;也難以想像一篇文章每逢緊要關頭,只會用成語來應付,因為那樣的作家只能靠古人來思想,拾古人的牙慧。滿口成語的人似乎油嘴滑舌,反之,絕口不用成語的人卻要費許多脣舌。大凡夠格的作家,都會酌量地驅遣成語。
「惟成言之務去」,是散文大家韓愈的主張。敏捷的作家要活用成語而不拘泥於成語,就應該悟出如何因勢導勢,借力使力,以我之四兩,撥彼之千斤。活用成語,就如向傳統借本錢,加些巧力,來賺創造的利息,其妙正如活用典故,務必化古為今,推陳出新。如此移花接木,讀者見了,似曾相識,就如見到熟人的孩子,認得出很像他父親,卻另有自己的幾分可喜。
這種戲擬的手法,英文叫做parody,王爾德乃其中高手。前文我曾舉英文成語,說婚後的日子,「兩人成伴,三人就亂。」(Two iscompany, three is none.)王爾德卻戲言三角關係之妙,竟說「三人才有伴,兩人不作算。」(Three is company, and two is none.)他諷刺婚姻,又說「離婚乃天作之分。」(Divorces are madein heaven.),而夫妻當眾調情是「乾淨內衣當眾洗。」(wash one’s clean linen in public)
莎士比亞的名劇《仲夏夜之夢》,曾有人加上一字,成了「仲夏夜之夢遺」,真是調皮,卻無法英譯。美國詩人吉爾默(Joyce Kilmer)寫樹的名句:「Poems are made by fools like me,∕But onlyGod can make a tree.」被諧詩鬼才納許(Ogden Nash)輕輕一扭,就成了妙趣:「Poems are made by fools like me,∕But onlyGod can make a trio.「樹」一扭成了「三重奏」,原來是影射聖三位一體(The Trinity),十分好笑。
我翻譯王爾德的喜劇《不可兒戲》,碰到處這麼一段話:You should get married. A misanthrope I can understand──a womanthrope, never!這是勞小姐勸蔡牧師結婚的一段話,不幸她咬文嚼字,把misogynist(憎恨女性者)誤說成womanthrope,卻妙在與前文的misanthrope同一格式。如果我不求變通,只將就直譯成「一個厭世者我可以了解──一個厭女者,決不!」聽眾一定茫然。結果我乞援於中文的四字成語格,把英文的名詞變通為中文的短句:「一個人恨人類而要獨善其身,我可以了解─一個人恨女人而要獨抱其身,就莫名其妙!」「獨善其身」原為成語,「獨抱其身」卻是將「抱獨身主義」的意思鑄入「獨善其身」的語法而得來的。
《不可兒戲》裡另有一處,兩個好友談到鄉下生活;亞吉能問鄉下來的傑克,在鄉下他逗什麼樣的人開心,傑克輕描淡寫地答道:O neighbors, neighbors.我的中譯仍然要靠自然而又好懂的四字成語。所以我譯成:「哦,左鄰右舍呀。」如果直譯成「哦,鄰居,鄰居。」就太奇怪了。
該劇又有一處,巴夫人盤問追求她女兒的少年:「我一向認為,有意結婚的男人,要嘛應該無所不知,要嘛應該一無所知。你是哪一類呀?」傑克猶豫了一下說:「我一無所知。」前一句的原文是……should know either everything or nothing,後一句則是I know nothing。如果譯成「應該什麼都知道或什麼都不知道」,就太囉嗦、太稚嫩了。足見對付英文或其他西文的名詞,尤其是抽象名詞,還得動用中文的短句,尤其是簡潔有力的四字成語。
6我有一本近著,書名《含英吐華》,評論的正是英文作品應如何中譯,但其四字句法卻本於成語「含英咀華」。我只改了一個字,原句的「英、華」就變成了英文與中文:進口的是英文,出口時卻是中文了。所以成語之為用大矣,不但可以原封照搬,更可器官移植,託古改今,與時並進,而更活潑了、豐富了中文。
我另有一本書,名叫《井然有序》,收集的都是為他人所寫的序言。這四字成語原封不動,但「序」字的意思卻擴大了。我的散文集《日不落家》,書名所套的「日不落國」之句,不是中文成語,而是一句英文,說大英之為帝國,殖民地遍布全球,陽光照處,必有英屬領土。一九九七年我家四個女兒,分別住在加拿大、美國、英國、比利時,而我們夫妻住在台灣,所以我們余家也稱得上是「日不落家」了。
此外,我的書名有四字成語架式的,尚有《五陵少年》、《白玉苦瓜》、《青青邊愁》、《分水嶺上》、《春來半島》、《隔水觀音》、《隔水呼渡》、《五行無阻》、《高樓對海》等多部。這四字句型,可說已經成為我書名的常用格式了。
為了寫這篇文章,我曾回顧自己的文體詩風,發現這四字句法,不論是單行或駢行,對我的語言風格都頗有貢獻。我曾說自己的語言是「白以為常,文以應變」,意思是用白話作基調,而酌用文言來變調,來調整彈性、速度、口吻與場景。所謂文言,不必高古深奧,但求穩健精簡,不必華辭麗采,但求言不虛發,辭無浪費。例如〈白玉苦瓜〉的最後幾行:
……一只仙果
不產在仙山,產在人間
久朽了,你的前身,唉,久朽
為你換胎的那手,那巧腕
千眄萬睞巧將你引渡
笑對靈魂在白玉裡流轉
一首歌,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
被永恆引渡,成果而甘
「千眄萬睞」是四字成語的新鑄,形容玉匠在真苦瓜與玉雕苦瓜之間反覆比對,務求將苦瓜的靈魂注入白玉。最後兩行的「是瓜而苦」與「成果而甘」,必須用文言無可再簡的句法,來逼出「生命賴藝術以昇華」的信念。而此一生死以之的信念,更有賴「瓜、苦、果、甘」四個字交相呼應的對仗與雙聲,才能堅持而達到結論。如果依一般新詩的稚嫩句法,把最後兩行寫成:「一首歌,曾經詠生命是一只苦瓜∕被永恆引渡,變成了甘果。」也算不錯了,但與文言的四字句法相比,就顯得太鬆、太淺了。
中國詩的句法始於四言之端莊,歷經五言與七言之奇偶交錯,相反相成,而終於長短句之伸縮多姿。但源頭這四字典型始終不衰,不但在七言詩中成為穩定大局的句頭,而且在四六駢文中高踞聯首,甚至在單行的古文中也往往成為壓陣的語法。一位現代作家,無論是要利用它、革新它、或是避免它,都不能不懂它在中文語法上的重要地位。
在我自己的散文之中,它也是一種重要的語型、句法。早期我的散文兼容英文句法,單行多於駢行,較少四字成語或四字句型。後期則有意「去英文化」,不但句子較短,而且駢散交錯,因此四字句型增多。評論我散文的學者,不少人肯定我的後期而質疑我的早期,恐怕這也是一大原因。早期的我,像大鬧天宮的孫悟空;後期的我,已成為唐僧的徒弟了。早期飛揚跋扈,不知為誰而雄。後期似乎「雅馴」多了,卻也太「馴」了吧。以下且從我前後期的文章裡,各引一段作為對照:
題目的現代化,是今日中國作家早該注意的問題之一。一個真正敏感的作家,應該將他纖細的觸鬚,伸到藝術的每一個角落。我們無法想像,一篇揚溢著現代精神的作品,居然肯戴上一頂發霉的帽子。
(摘自〈論題目的現代化〉,一九六三年)
幸蕙遍讀吾詩,發而為論,三年有成,即將出書,索序於我……幸蕙選詩,不盡「唯名是從」,往往反而「蕙眼獨具」,會挑出一些評家很少注目的「冷作」或未及注目的新作,令我驚喜。
(摘自〈悅讀陳幸蕙〉,二○○二年)
7四字成語或四字句型,盤踞中文已久,不但下筆好使,更且出口暢順,已經成為語法的一大基調,何況其中還有不少迄為民族智慧或民俗世故的載體,有些來頭很大,有些出處不明,所以不但讀書人善於驅遣,就算江湖市井之流也會引用幾句。身為作家如果不善驅遣成語,或是會用的成語十分有限,下筆怎能左右逢源?但另一方面,如果他不會自鑄新詞,自創佳句,遇到緊要關頭,只會依靠幾句四平八穩、人云亦云的陳腔老套來應付過關,那就會陷於成語而不能自拔,始終近不了創作。真正的高手應該把成語用在刀口上,將舊句引出新意,或是移花接木,將舊框嵌入新字,變出新趣。如此,才能激發民族語言的生機,使其長保活潑、生動。
至於成語與各種文類的關係,也值得討論。大致說來,詩貴獨創,可以利用四字語法來求變求新,但不宜原封照搬。小說的對話依人物的身分可酌用成語或俚語,但敘述的部分應加區別。戲劇的台詞求其順口易懂,不妨用些簡潔而響亮的成語;抽象而生硬的名詞,最宜用成語短句來化解。散文乃直接對讀者發言,就像斯文人從容不迫的談吐,用些成語當然可以,但是像斯文人的談吐富於機鋒或諧趣,也不妨把成語變成新腔。論文乃學者在發言,宜乎字斟句酌,所用成語應求其高雅端莊,即使引經據典,駢行偶對,亦無不可。雜文以短小精悍取勝,最忌扯淡費辭,多用成語不妨。童話最忌世故,應力戒成語。譯文多用成語,就會失去原文風味;像「朝秦暮楚」、「暗度陳倉」一類來自典故的成語,尤不可用。
2004-02-10╱中國時報╱第E7版╱人間副刊╱余光中
5新文學改用白話,不再寫文言,但是文言的智慧與語法卻靠數以千計的成語保留了下來,像一筆豐富的遺產,不用交稅,也無須兌現,口頭筆下,永遠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現金。
成語用在白話文裡,可以潤滑節奏、調劑句法、變化風格。我們很難想像,一篇文章能完全不用成語,因為那樣的文章必然累贅冗長;也難以想像一篇文章每逢緊要關頭,只會用成語來應付,因為那樣的作家只能靠古人來思想,拾古人的牙慧。滿口成語的人似乎油嘴滑舌,反之,絕口不用成語的人卻要費許多脣舌。大凡夠格的作家,都會酌量地驅遣成語。
「惟成言之務去」,是散文大家韓愈的主張。敏捷的作家要活用成語而不拘泥於成語,就應該悟出如何因勢導勢,借力使力,以我之四兩,撥彼之千斤。活用成語,就如向傳統借本錢,加些巧力,來賺創造的利息,其妙正如活用典故,務必化古為今,推陳出新。如此移花接木,讀者見了,似曾相識,就如見到熟人的孩子,認得出很像他父親,卻另有自己的幾分可喜。
這種戲擬的手法,英文叫做parody,王爾德乃其中高手。前文我曾舉英文成語,說婚後的日子,「兩人成伴,三人就亂。」(Two iscompany, three is none.)王爾德卻戲言三角關係之妙,竟說「三人才有伴,兩人不作算。」(Three is company, and two is none.)他諷刺婚姻,又說「離婚乃天作之分。」(Divorces are madein heaven.),而夫妻當眾調情是「乾淨內衣當眾洗。」(wash one’s clean linen in public)
莎士比亞的名劇《仲夏夜之夢》,曾有人加上一字,成了「仲夏夜之夢遺」,真是調皮,卻無法英譯。美國詩人吉爾默(Joyce Kilmer)寫樹的名句:「Poems are made by fools like me,∕But onlyGod can make a tree.」被諧詩鬼才納許(Ogden Nash)輕輕一扭,就成了妙趣:「Poems are made by fools like me,∕But onlyGod can make a trio.「樹」一扭成了「三重奏」,原來是影射聖三位一體(The Trinity),十分好笑。
我翻譯王爾德的喜劇《不可兒戲》,碰到處這麼一段話:You should get married. A misanthrope I can understand──a womanthrope, never!這是勞小姐勸蔡牧師結婚的一段話,不幸她咬文嚼字,把misogynist(憎恨女性者)誤說成womanthrope,卻妙在與前文的misanthrope同一格式。如果我不求變通,只將就直譯成「一個厭世者我可以了解──一個厭女者,決不!」聽眾一定茫然。結果我乞援於中文的四字成語格,把英文的名詞變通為中文的短句:「一個人恨人類而要獨善其身,我可以了解─一個人恨女人而要獨抱其身,就莫名其妙!」「獨善其身」原為成語,「獨抱其身」卻是將「抱獨身主義」的意思鑄入「獨善其身」的語法而得來的。
《不可兒戲》裡另有一處,兩個好友談到鄉下生活;亞吉能問鄉下來的傑克,在鄉下他逗什麼樣的人開心,傑克輕描淡寫地答道:O neighbors, neighbors.我的中譯仍然要靠自然而又好懂的四字成語。所以我譯成:「哦,左鄰右舍呀。」如果直譯成「哦,鄰居,鄰居。」就太奇怪了。
該劇又有一處,巴夫人盤問追求她女兒的少年:「我一向認為,有意結婚的男人,要嘛應該無所不知,要嘛應該一無所知。你是哪一類呀?」傑克猶豫了一下說:「我一無所知。」前一句的原文是……should know either everything or nothing,後一句則是I know nothing。如果譯成「應該什麼都知道或什麼都不知道」,就太囉嗦、太稚嫩了。足見對付英文或其他西文的名詞,尤其是抽象名詞,還得動用中文的短句,尤其是簡潔有力的四字成語。
6我有一本近著,書名《含英吐華》,評論的正是英文作品應如何中譯,但其四字句法卻本於成語「含英咀華」。我只改了一個字,原句的「英、華」就變成了英文與中文:進口的是英文,出口時卻是中文了。所以成語之為用大矣,不但可以原封照搬,更可器官移植,託古改今,與時並進,而更活潑了、豐富了中文。
我另有一本書,名叫《井然有序》,收集的都是為他人所寫的序言。這四字成語原封不動,但「序」字的意思卻擴大了。我的散文集《日不落家》,書名所套的「日不落國」之句,不是中文成語,而是一句英文,說大英之為帝國,殖民地遍布全球,陽光照處,必有英屬領土。一九九七年我家四個女兒,分別住在加拿大、美國、英國、比利時,而我們夫妻住在台灣,所以我們余家也稱得上是「日不落家」了。
此外,我的書名有四字成語架式的,尚有《五陵少年》、《白玉苦瓜》、《青青邊愁》、《分水嶺上》、《春來半島》、《隔水觀音》、《隔水呼渡》、《五行無阻》、《高樓對海》等多部。這四字句型,可說已經成為我書名的常用格式了。
為了寫這篇文章,我曾回顧自己的文體詩風,發現這四字句法,不論是單行或駢行,對我的語言風格都頗有貢獻。我曾說自己的語言是「白以為常,文以應變」,意思是用白話作基調,而酌用文言來變調,來調整彈性、速度、口吻與場景。所謂文言,不必高古深奧,但求穩健精簡,不必華辭麗采,但求言不虛發,辭無浪費。例如〈白玉苦瓜〉的最後幾行:
……一只仙果
不產在仙山,產在人間
久朽了,你的前身,唉,久朽
為你換胎的那手,那巧腕
千眄萬睞巧將你引渡
笑對靈魂在白玉裡流轉
一首歌,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
被永恆引渡,成果而甘
「千眄萬睞」是四字成語的新鑄,形容玉匠在真苦瓜與玉雕苦瓜之間反覆比對,務求將苦瓜的靈魂注入白玉。最後兩行的「是瓜而苦」與「成果而甘」,必須用文言無可再簡的句法,來逼出「生命賴藝術以昇華」的信念。而此一生死以之的信念,更有賴「瓜、苦、果、甘」四個字交相呼應的對仗與雙聲,才能堅持而達到結論。如果依一般新詩的稚嫩句法,把最後兩行寫成:「一首歌,曾經詠生命是一只苦瓜∕被永恆引渡,變成了甘果。」也算不錯了,但與文言的四字句法相比,就顯得太鬆、太淺了。
中國詩的句法始於四言之端莊,歷經五言與七言之奇偶交錯,相反相成,而終於長短句之伸縮多姿。但源頭這四字典型始終不衰,不但在七言詩中成為穩定大局的句頭,而且在四六駢文中高踞聯首,甚至在單行的古文中也往往成為壓陣的語法。一位現代作家,無論是要利用它、革新它、或是避免它,都不能不懂它在中文語法上的重要地位。
在我自己的散文之中,它也是一種重要的語型、句法。早期我的散文兼容英文句法,單行多於駢行,較少四字成語或四字句型。後期則有意「去英文化」,不但句子較短,而且駢散交錯,因此四字句型增多。評論我散文的學者,不少人肯定我的後期而質疑我的早期,恐怕這也是一大原因。早期的我,像大鬧天宮的孫悟空;後期的我,已成為唐僧的徒弟了。早期飛揚跋扈,不知為誰而雄。後期似乎「雅馴」多了,卻也太「馴」了吧。以下且從我前後期的文章裡,各引一段作為對照:
題目的現代化,是今日中國作家早該注意的問題之一。一個真正敏感的作家,應該將他纖細的觸鬚,伸到藝術的每一個角落。我們無法想像,一篇揚溢著現代精神的作品,居然肯戴上一頂發霉的帽子。
(摘自〈論題目的現代化〉,一九六三年)
幸蕙遍讀吾詩,發而為論,三年有成,即將出書,索序於我……幸蕙選詩,不盡「唯名是從」,往往反而「蕙眼獨具」,會挑出一些評家很少注目的「冷作」或未及注目的新作,令我驚喜。
(摘自〈悅讀陳幸蕙〉,二○○二年)
7四字成語或四字句型,盤踞中文已久,不但下筆好使,更且出口暢順,已經成為語法的一大基調,何況其中還有不少迄為民族智慧或民俗世故的載體,有些來頭很大,有些出處不明,所以不但讀書人善於驅遣,就算江湖市井之流也會引用幾句。身為作家如果不善驅遣成語,或是會用的成語十分有限,下筆怎能左右逢源?但另一方面,如果他不會自鑄新詞,自創佳句,遇到緊要關頭,只會依靠幾句四平八穩、人云亦云的陳腔老套來應付過關,那就會陷於成語而不能自拔,始終近不了創作。真正的高手應該把成語用在刀口上,將舊句引出新意,或是移花接木,將舊框嵌入新字,變出新趣。如此,才能激發民族語言的生機,使其長保活潑、生動。
至於成語與各種文類的關係,也值得討論。大致說來,詩貴獨創,可以利用四字語法來求變求新,但不宜原封照搬。小說的對話依人物的身分可酌用成語或俚語,但敘述的部分應加區別。戲劇的台詞求其順口易懂,不妨用些簡潔而響亮的成語;抽象而生硬的名詞,最宜用成語短句來化解。散文乃直接對讀者發言,就像斯文人從容不迫的談吐,用些成語當然可以,但是像斯文人的談吐富於機鋒或諧趣,也不妨把成語變成新腔。論文乃學者在發言,宜乎字斟句酌,所用成語應求其高雅端莊,即使引經據典,駢行偶對,亦無不可。雜文以短小精悍取勝,最忌扯淡費辭,多用成語不妨。童話最忌世故,應力戒成語。譯文多用成語,就會失去原文風味;像「朝秦暮楚」、「暗度陳倉」一類來自典故的成語,尤不可用。
2004-02-10╱中國時報╱第E7版╱人間副刊╱余光中